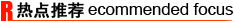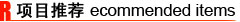我認(rèn)為,在追問建筑的本質(zhì)之時,應(yīng)該從新的城市生活的真實,而不是從形式主義的操作開始。這十年左右,我們嘆息于在這樣慘烈的消費生活的增幅作用中失去的現(xiàn)實。我們?nèi)缤酒烦砂a患者沉溺于毒品中一般,感覺在社會中自己的身體不斷被侵蝕,仿佛被帶入到了幻影的虛構(gòu)中一樣。電視流行的時期,隨身聽、家用電腦風(fēng)靡全球的時期都是如此。咖啡吧的大餐桌在年輕人聚集的地方大量出現(xiàn)的時期也是如此,冷凍食品專柜在二十四小時營業(yè)的便利店中出現(xiàn)的時期也是如此。所有人都感覺到,電視和家用電腦從餐室奪走了最原始的家庭交流。感覺到了咖啡吧的金屬或石制的巨大的餐桌,將烤串店內(nèi)熱烈而粗俗的爭論換成了關(guān)于炫酷時尚的食物的話題。感覺到了隨身聽爆炸性的熱賣將年輕人封閉在更加孤獨的世界。
的確我們都覺得,生身的肉體和精神正在游離,失去了生活的真實。察覺到自然,將人類濃稠的血液送入處理廠的生活,溝通正在解體的喪失感,無疑這就是空虛的感覺。一直到過剩,物品越是泛濫,喪失感和空虛越是增加,有想法的建筑師對這樣的狀況感到憤怒,批判消費,堅持徹底抵抗。年輕的建筑師對此并無感覺,也沒有批判,對此的憤怒我也體會到了。如同八束始所嘆息的那樣(《超越虛無主義》,《新建筑》,一九八九年九月號),建筑系的學(xué)生對于生活真實的缺乏,膚淺的時尚的形式主義的追隨,對于這些憤怒的感情,我也體會到了。
誠實說,這樣憤怒的感覺并非從未有過,但是最近卻覺得,即使要批判這種狀況也無從下手。空虛的消費符號日益增加,有自閉癥氣質(zhì)的建筑系學(xué)生也在增加,但是開始覺得在其中也許能夠看到新的城市生活的真實。就算再怎么要叫自閉癥氣質(zhì)的學(xué)生更加開朗地生活,也仿佛是關(guān)掉電視,叫邊看電視邊吃漢堡的小孩子和家長邊說話邊吃飯一樣。與其這樣,我們其實更應(yīng)該找到一張能夠好好享受漢堡的美味的餐桌吧。與其討厭咖啡吧的大餐桌,死守在烤串店的柜臺,不如在咖啡吧的大餐桌發(fā)現(xiàn)新的真實吧。每當(dāng)我坐在花崗巖或者金屬制的大餐桌前,都想要將付著在上面的帶來快感的消費符號剝下,做成在宇宙中漂浮一般的無厚度無重量的圓盤一般的餐桌。在那張大餐桌的邊上,想要大家一起圍著一張大餐桌吃喝的原始的欲求,和顧盼四周,對能夠與素不相識的面孔也能喝酒的孤獨的欲求混在一起。被置換成了懷舊與潮流糾纏起來的疑似物的存在感。放開這種四不像的狀態(tài),向著虛幻得讓人覺得恐怖的世界,將物體消除。感覺真實并不在消費的面前,而是只存在于超越消費的彼岸。所以在這片消費之海面前的我們,只能浸入水中,向?qū)Π队稳フ覍な裁矗酥獠o他法。如果只站在海岸邊看著,水位只會越來越高,因此無法拒絕游泳,也不能茫然地被海水吞沒。
但是,盡管充滿空虛符號的消費主義的當(dāng)代社會將我們的身體變成冷酷的仿生機器人一般,有趣的是我們不斷探尋人生最根源的行為的事實。將吃飯這件極為原始卻單純的行為徹底觸發(fā)的社會真的到了這個程度嗎?過度的復(fù)雜,過度的虛飾,窮盡想象的界限,消費社會逼近餐飲,窮追不舍。城市中的餐館每天以難以置信的速度開張,變動。百貨商場的食品賣場堆滿了亮晶晶的食物,雜志和電視中關(guān)于食物的信息,這些完全像希區(qū)柯克的《鳥》一樣襲擊人們,將人們吃個精光。如此這般慘烈。
如同吉本芭娜娜的處女作《廚房》及之后的《滿月——廚房2》的標(biāo)題一樣,有關(guān)吃飯一事,對日常的描寫貫穿始終。與故事情節(jié)的展開無關(guān),主人公都是在廚房邊做飯或者邊洗碗邊對話。永遠都在吃飯。
“夜色開始變得透明的時候,我們開始大吃特吃晚飯。沙拉、派、燉鍋、炸土豆餅,炸豆腐、泡菜、涼拌雞肉粉絲、基輔湯、醋豬肉、燒麥……雖然國籍亂作一堆,我們卻并不在意地吃了很久,一邊喝著酒,全部吃光了。 ”
又或是在深夜奔向便利店。
“夜里我睡不著,跑去便利店買布丁,結(jié)果進門的地方,剛好下班的惠理子和在店里工作的其實是男生的女生們,用紙杯喝著咖啡,吃著關(guān)東煮。我喊惠理子!她就拉起我的手,笑著說,哎呀,離開我們家以后瘦了不少呀。她穿著藍色的連衣裙。 我買完布丁出來,惠理子一手拿著紙杯,熱烈地望著在黑暗中閃光的街道。我開玩笑說惠理子的表情像男生一樣啊。惠理子一下笑了起來,說,哪里,咱家的姑娘胡說八道,莫非是到了青春期了。我回答說,我明明已經(jīng)是大人了,店里的女生都笑了。然后……說再到家里來玩啊,哎呀太棒了,笑著告別了,那就是最后一次見到她了。”
毫無顧慮地吃,毫無保留地聊天。實際上是充滿生命力地在說話。實際上其中洋溢著豐富的感受力。對人完全信賴。生活在消費主義的正中間,卻毫不勢利,也沒有被消費的洪流卷走,對人類肯定。充滿了豐富的嶄新的真實。
難道做不出像吉本芭娜娜的小說那樣具體的、充滿生機的纖細的建筑嗎,我在某本雜志的專欄這樣寫了之后,上文中引用的鈴木隆之在一起喝酒的地方反擊我。兩個人都醉到不行的時候,雖然還沒開始辯論,但是提到了類似“她的小說的世界觀還沒有分化形成”的意思。的確,換作親身創(chuàng)作小說的鈴木來說,沒有世界觀的世界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作為小說成立,肯定是日日夜夜不停思考的問題。自然也無法忍受對世界觀或者文學(xué)等等概念缺乏自覺性的少女的文章受到如此無保留的褒揚這件事情。對我來說,建筑的世界中唯獨關(guān)心的是建筑的本質(zhì)。因此,要是想芭娜娜的小說一樣的建筑出現(xiàn)了,我大概要發(fā)出和鈴木一樣的呼喊了。盡管如此,僅在那么具體的日常對話中,就包含了那么豐富的內(nèi)容,實在無法不為她的誠摯而感動。
最近為了在布魯塞爾舉辦的展覽,做了名為“東京游牧少女的包-2”的原尺寸大的模型。其實也應(yīng)該叫做三年前做的模型的修改版,之前的那個是用半透明的布來表現(xiàn)蒙古包的家的形狀,這次用多面體制作了如同太空船一般漂浮在空中的模型。雖然也可以說是更加未來感的表現(xiàn),但是在這個差別中表現(xiàn)了我心中的城市生活的想象的差別。也就是說三年前,我誠然是很犬儒的。漂亮地委身于時尚的空間中,大吃特吃,在消費最前線享受城市生活之樂,我覺得當(dāng)時一半的我是對這些抱有憧憬,另一半的我則是無法擺脫自覺性的缺失。但是對于這次的游牧少女,我期待能從未來的城市空間中發(fā)現(xiàn)新的真實,開拓具有未來感的城市生活。因此,希望住進去的少女能夠擁有芭娜娜的小說主人公一般的感受力。
然后去年,仍然是為展覽制作了架空項目“地上12m的樂園”,設(shè)想了在東京上空漂浮的游牧少女的包,能夠在現(xiàn)有的街道地區(qū)上空滑翔,在建筑物的屋頂變成閣樓的姿態(tài)。這個項目同樣是對現(xiàn)實的城市生活稍作加工,是希望能夠制作出雖然短暫,但是能吹走懷舊,享受開放的、生機勃勃的城市生活的空間的結(jié)果。希望即使是自閉癥氣質(zhì)的男生也會被此吸引,而毫不猶豫地盡情享受原始的未來的生活。
于是,接下來的步驟就是將如此獲得的城市生活的意象轉(zhuǎn)換為建筑空間的任務(wù)了。但是,這里既沒有什么追求嶄新的表現(xiàn)形式的苦惱,也說不上熱情滿滿吧。太過于追求表現(xiàn)力,很有可能陷入形式主義的陷阱,反而會像前述一樣被消費掉。總之,最后決定將生活的意象插入既有的建筑空間中。之后將已經(jīng)閉鎖的建筑空間到處開洞,讓新的城市的風(fēng)、空氣、光線全部進去。生活的意象仿佛建筑空間的炸藥。這樣,就能讓既有的空間稍稍偏離,變成另外的空間。反復(fù)進行這個偏曲的過程中,肯定能在新的城市生活的真實中生出新的建筑。對建筑越是固執(zhí),我們越是能樂觀地享受,最后也終將超越我們的城市生活。
文章來源:伊東豐雄《不浸入消費之海就沒有新建筑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