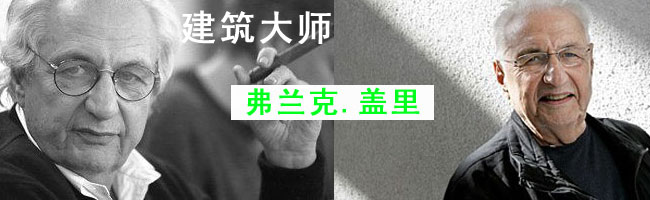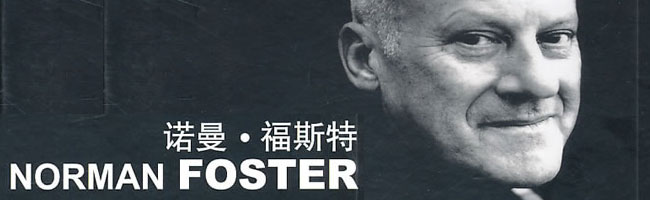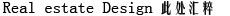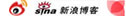路易斯·康 Louis Isadore Kahn
出生年月:1901年2月20號
國籍: 美國 出生地: 愛沙尼亞的薩拉馬島
畢業(yè)院校: 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(xué)
路易斯.康被譽為建筑界的詩哲,大器晚成的他五十多歲時才真正成為一代宗師,他的建筑作品通常是在質(zhì)樸中呈現(xiàn)出永恒和典雅,而這次在萊斯大學(xué)的講演則闡述了建筑應(yīng)該怎樣在反映人類對本質(zhì)的思考過程中創(chuàng)造的奇跡;他在演講時提到的光明與陰影,與他在建筑作品中善于把握光的作用一樣,都啟發(fā)著人們對存在和哲理的思考。通過他的描述,我們可以感知建筑學(xué)的真諦——對超越物質(zhì)與技術(shù)而存在的人類的夢想的表達(dá)。
路易斯·康發(fā)展了建筑設(shè)計中的哲學(xué)概念,認(rèn)為盲目崇拜技術(shù)和程式化設(shè)計會使建筑缺乏立面特征,主張每個建筑題目必須有特殊的約束性。他的作品堅實厚重,不表露結(jié)構(gòu)功能,開創(chuàng)了新的流派。
個人簡介:
1974年3月18日,紐約,賓夕法尼亞火車站,工作人員在巡邏時發(fā)現(xiàn)車站廁所里有一位突然離世的老人,死因是心臟病突發(fā)。他的護(hù)照地址被涂掉了,于是只能被送往市立停尸中心,三天之后,人們才終于找到了他的身份——路易·艾瑟鐸·康(Louis Isadore Kahn)。就在18日上午,美國建筑師斯坦利·泰格曼(Stanley Tigerman)還在倫敦希思羅機場與路易·康偶遇。泰格曼回憶道:“我在機場看到這位老人,他看上去像是視網(wǎng)膜脫落似的,真的非常狼狽。他說:‘我對生活知道的是那么少。除了建筑之外我什么都不會做,因為它是我知道的全部內(nèi)容。”這幾乎是康最后的留言,對自己的一生做了一個簡明扼要、無比坦誠的總結(jié)。
1901年2月20日,康出生在波羅的海的薩列瑪島。這是愛沙尼亞的一座小島,當(dāng)時處于波蘭統(tǒng)治下。康,是一個猶太家庭的“姓”。路易的父親是一名虔誠的猶太教徒,母親伯莎出身名望甚高的門德爾松家族。伯莎·康與德國浪漫主義作曲家費列克斯·門德爾松是親戚。路易·康自幼年起就處于他雙親的文化熏陶之下。自然、宗教、音樂,以及歌德、席勒等人的文學(xué)作品,是康的精神食糧。
路易·康一家于1906年移民美國。1912至1920年間,他先后在費拉德爾菲亞中心和公立工業(yè)藝術(shù)設(shè)計學(xué)校求學(xué),并于1919年進(jìn)入賓夕法尼亞大學(xué)攻讀建筑系。在那里,他接受了古典主義建筑教育,目睹了現(xiàn)代主義建筑運動的狂飆突進(jìn)。他和中國第一代歸國建筑師楊廷寶當(dāng)過同班同學(xué),作為當(dāng)時班上成績最不起眼的那幾個學(xué)生之一(而楊廷寶一直是優(yōu)等),康說道,他每次設(shè)計作業(yè)都要做兩份,一份交給學(xué)校,另一份才是真正他想做的。
1935年起,路易·康開設(shè)了獨立的事務(wù)所。自大蕭條時期,與一些城市規(guī)劃工作者,如克萊侖斯·斯登、亨利·萊特等人建立起來的友誼,也使康有機會從事一些城市開發(fā)性設(shè)計。在將近20年的經(jīng)歷中,他的生活是一段并不令人羨慕的苦斗。
“康沒日沒夜地與繪圖員一起工作。嘴里不是一支雪茄,就是一支卷煙。手中是一支軟鉛筆或炭棒。他總是一邊敘述著自己的理論、原則,一邊一遍又一遍地在草圖上畫上永無休止的線條。有時,一個成熟的念頭隨著鉛筆或炭筆逐漸明晰地出現(xiàn)在紙上。有時,可能依然是一紙混沌,有待于繪圖員再畫成草稿來和路易·康作另一輪摸索。”繪圖員惠斯回憶道,而這些沒日沒夜的工作換來的卻是默默無聞和50歲時還憂慮于找不到一個滿意的設(shè)計。
50歲以后的康開始了他的傳奇人生,以1953年耶魯大學(xué)美術(shù)館的設(shè)計而嶄露頭角。此后則是費城賓州大學(xué)醫(yī)學(xué)研究實驗中心(1957)、孟加拉國達(dá)卡政府建筑群(1962)、紐約州羅徹斯特基督教唯一神教派第一教堂(1963)、得克薩斯州沃思堡金貝爾美術(shù)館(1972),每一個都可以稱作是建筑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,并為路易·康贏得了世界性聲譽。以50多歲的年紀(jì)猛然從小角色成長為大宗師——不能不說,路易·康,成為了一個時代的奇跡。
磚想要成為拱
你對一塊磚說:“你想要什么,磚?”磚對你說:“我喜歡一個拱券。”你對磚說:“瞧,我也想要一個,但拱券花錢最多,也不好做。我想你可以將就,用混凝土架在開口的上端,效果也一樣好呀。”然后磚回答:“我想你說得對,但是假若你問我想要什么?我想要拱啊!”
以上這段文字是康著名的與磚的對話,也是康與別人討論建筑和建筑理論時的文字風(fēng)格,有很多人覺得不知所云,或者認(rèn)為他故弄玄虛。康喜歡用哲學(xué)化的語言來討論建筑,為了準(zhǔn)確表達(dá)他的觀念,康不惜創(chuàng)造新字,更甚而改變句型結(jié)構(gòu),以文句之詩意傳達(dá)深沉的理念。康不是思路不清,也絕非故弄玄虛,因為康相信“未完成性”的力量。他認(rèn)為任何一件作品均是未完成的。“人永遠(yuǎn)比作品偉大,因為人永遠(yuǎn)無法充分表現(xiàn)他的企圖”,而“知識也是未完成的一本書,知識也知曉它的未完成性”。
歷史的穿行者
康在20世紀(jì)建筑藝術(shù)中的地位是重要而特殊的,他完整地涵蓋了整個西方文明構(gòu)架的主要組成部分:希臘神話(哲學(xué))、宗教精神以及工業(yè)科學(xué),他不在乎任何建筑風(fēng)格,他是輻射中心,亦如線貫明珠。他包容萬千,他曾沐浴過學(xué)院派的古典教育,又熱衷于預(yù)制混凝土、懸鎖、薄殼、懸臂等結(jié)構(gòu)施工技術(shù)的應(yīng)用。
康熱愛開端,一切形式的開端,生命初現(xiàn)的開端,他曾經(jīng)說過:“我愛起點,我更為起點驚嘆,”他又補充道:“我一再說我經(jīng)常追求源泉起點,在我的性格中總想發(fā)現(xiàn)起點。”他曾在談到英國史時說:“事實上我的真正目的是讀零卷,那是不曾寫出來的(也是無法寫出來的東西)。”他說:“因此我相信建筑師在某種程度上必須回過頭去聆聽最初的聲音。”這最初的聲音, 就是建筑及其空間得以生成的文化源頭,在源頭之處事物沒有受到任何來自于人類文化(因為當(dāng)時的文化尚未形成)的影響,事物或?qū)嵤碌拇嬖诙际且员菊娴脑鷳B(tài)狀態(tài)而出現(xiàn)。他的建筑哲學(xué)最大宗旨似乎想穿越人類建筑文明的覺醒所造成的迷障,而直接降落在事物天真無邪的狀態(tài)中去。與其說康在與整個建筑歷史相對抗,不如說在與人類建筑文化相對抗。